1979年8月华盛顿子弹队访华:埃尔文-海耶斯的别样态度
1979年8月,一辆大巴驶至长城之畔,华盛顿子弹队的负责人艾比-波林立誓,今后球队将不再进行海外之旅。令波林心生不悦的是,大巴车上的子弹队球员埃尔文-海耶斯与大卫-科尔金不愿下车。不知趣的海耶斯向老板直言,“我曾目睹过那座雄伟的长城。”
维斯-昂塞尔德,这位历史专业的大学学子,多少显得有些尴尬,他向海耶斯建议道:“这可是人类在外太空中唯一可见的建筑啊!”
海耶斯不为所动:“我永远不会去外太空。”
然而,海耶斯仍需陪同他人前往若干地点,诸如入住那家缺乏空调设施、被誉为“北京第二佳酒店”的住所,这一切皆因“北京首屈一指的酒店”已被当时担任美国副总统的沃尔特-蒙代尔所占据。
子弹队于1978年6月经过抢七大战击败超音速,成功夺冠。胜利的喜悦还未完全消散,波林便带着球队成员及其家属踏上了前往以色列的旅程。然而,这位意犹未尽的老板却突然有了更进一步的打算,于是他向美国国务院的友人吐露了自己的心声:“我打算带领球队前往中国。”
三个月过后,国务院的友人携来一封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发出的邀请函,而此时距离确立邓小平在中共党内核心地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尚有三个月的时间。值得一提的是,就在那年的九月,大卫-斯特恩卸任了他担任了12年的NBA外部法律顾问一职,转而成为了NBA的副总裁。
自1971年美国乒乓球队踏足我国土地,中美两国在体育领域的交流日益活跃。美国陆续向我国派遣了多元化的运动队伍,诸如跳水、篮球、足球和排球等,种类繁多。在这样的背景下,中美关系迅速升温,这一历史性事件被称作“乒乓外交”。值得一提的是,子弹队作为首支访问我国的专业运动队伍,在改革开放全面启动之前,这样一个具有浓厚商业色彩的组织突然降临我国,其背后的意义不言自明。
子弹队经过日本、香港的转机抵达北京,开始了为期13天的中国之旅,于是他们自然要与中国球队进行一场较量。在北京,他们遭遇的是八一队,这支球队在五个月前曾两次击败了来访的美国大学生明星队。给子弹队球员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身高2米21、体重超过150公斤的穆铁柱。海耶斯评价张伯伦是他所遭遇过的最庞大的球员,然而他认为张伯伦虽大,但穆铁柱却是真正的大个子,“穆,是BIG。”昂塞尔德坚信穆铁柱的身高至少有2米3,这和后来的NBA官方记录中姚明的身高7英尺6英寸相仿。而球队的主教练迪克-莫塔给出的数据则更为惊人,他声称穆铁柱的身高达到了7英尺8英寸,即2米34。
穆铁柱比赛资料图
莫塔的真正兴趣并不在此。在子弹队以96比85击败八一队的比赛中,赛后他与子弹队的法律顾问大卫-斯诺斯探讨了将八一队的郭永林引入NBA的可能性。这位24岁的辽宁籍球员,仅加入八一队一年,便已成为球队和国家队的关键得分手。作为前锋,他擅长跳投,被誉为“神投手”。在此次友谊赛中,他更是以全场最高的27分闪耀全场。
斯诺斯此行的另一项使命,便是根据联盟的规定,草拟了一份简短的合同,规定中国的“转播方”需支付一美元以获得这场比赛的转播权。斯诺斯事后回忆说,“他们从未履行过付款承诺。然而,他们向我透露,大约有五亿观众观看了我们的比赛。”
比赛结束之后,子弹队和八一队一同出席了邓小平为欢迎蒙代尔而设的宴会。杰里-萨克斯作为冠军球队的总裁,他的洞察力堪称一流。在宴会尽兴而归时,他不仅带走了桌上的筷子和菜单,还拿走了邓小平和蒙代尔的桌牌。他笑着说:“邓小平对篮球情有独钟。”
中美关系在这一年或许达到了巅峰,亦标志着新时代的辉煌起点——1979年的钟声敲响之际,中美两国正式开启了外交关系的大门。伴随着这一关系的飞跃,除了体育领域的交流和经济合作的深化,文化领域的互动也迎来了它的黄金十年。翻译充当着文化交流的纽带,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文字翻译领域迎来了清末民初之后的又一高峰。据数据统计,在1978至1987年这段时间里,社会科学领域的译作数量超过了5000种,这一数字是新中国成立前30年的十倍之多。文学翻译领域同样呈现出类似的繁荣景象,大量引进的译作主要源自当时的世界文化新中心——美国。在1979年之前,我国对美国的文学进行翻译推广的30年间,留下了鲜明的时代印记,主要翻译的是以批判现实主义为特点的无产阶级文学作品。
这种摒弃文学色彩的阶级批判翻译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延续至80年代初。1982年5月,北京出版社出版了《一个美国篮球明星的故事》一书,这本共计586页的薄册定价仅为1.8元。在书的封底,出版说明依旧鲜明地指出:“书中对美利坚社会各阶层的生活进行了细致描绘,呈现了在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下堕落、腐败的生活画面。”
在1972年3月,大卫-沃尔夫出版了其原著《犯规!康尼-霍金斯的故事》,然而,《纽约时报》对该书的评价并不算特别积极;至少,就中国译者所理解的“揭露”层面来看,其表现尚显不足。
霍金斯,这位1992届名人堂成员,其篮球生涯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曾因涉嫌莫利纳斯赌球案,被NBA以莫须有的理由拒之门外。然而,多年之后,他通过申诉成功重返NBA,并在那里展现出了卓越的竞技状态。霍金斯的故事原本就引人入胜,沃尔夫也的确努力描绘了底层黑人天才少年在商业机器下遭受无情打压的残酷现实,这正与中国译者所描述的“堕落腐朽的画面”相吻合。然而,美国书评人对这一观点持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沃尔夫在书中过多地穿插了更衣室内的八卦和篮球技巧的描述,这些看似“细腻”的细节描写,反而削弱了叙事的主线,给读者带来了额外的阅读负担,使得原本可以成为一部深刻的社会批判之作,沦为了普通球员传记。”
沃尔夫的这部作品在写作技巧上显得有些繁复,这仅仅是人们批评其的一个方面。然而,最让书评人们感到质疑的是,书中流露出的过分“谄媚”气息。霍金斯在经历了不公正的待遇后,成功踏入职业联盟的过程确实令人鼓舞,但沃尔夫似乎过分夸大了他在NBA的表现。他几乎把霍金斯塑造成了一位无敌的球星,一个时代的巨星,以及一位深受爱戴的英雄。沃尔夫的卓越并非问题所在,真正的问题在于他在描述中加入了众多定性评价。对于这种在传奇故事上镶上金色边框的做法,《纽约时报》的书评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读者无需他人告知球员的优劣,他们有自己作出判断的能力。”
尽管存在诸多不足,但远隔重洋的译者却认为,这部体育人物的传记在写作技巧上仍然充满新意;在书的封底,译者向中国读者介绍道,这正是西方所谓的新闻文学。往昔的翻译者们或许未曾料想,“新闻文学”在日后将以“新新闻主义”或“非虚构写作”的形式,成为我国自媒体时代新闻写作的显学。当然,民间对此的称呼或许有所差异,有人将其称作“特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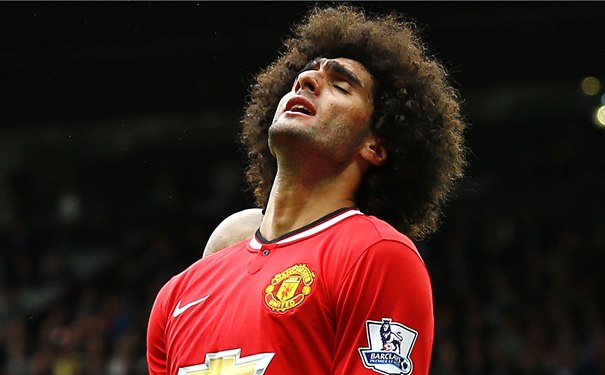
实际上,当沃尔夫着手撰写这部球员传记之际,美国的“非虚构写作”领域尚处于起步阶段。杜鲁门-卡波特,这位在1966年创作《冷血》的作家,自称是该流派的奠基人。而紧随其后,汤姆-沃尔夫在两年内追随嬉皮士潮流,创作了《刺激酷爱迷幻考验》。他与几位志同道合者共同开创了“新新闻主义”,其中便包括了盖伊-特立斯。
目前,在中国,广大普通读者对他所著的《被仰望与被遗忘的》、《邻人之妻》以及《王国与权力》这三部作品较为熟知。在1966年,34岁的特立斯担任体育撰稿人,他陆续创作了《辛纳屈感冒了》和《英雄的沉默赛季》两部作品,这两部作品与1962年出版的《五十岁的乔-刘易斯》共同组成了“英雄三部曲”。其中,《辛纳屈感冒了》和《英雄的沉默赛季》这两部作品,被大卫-哈伯斯塔姆高度评价为“20世纪最杰出的娱乐与体育特写”的前两部。《英雄的沉默赛季》这部作品,则是以美职棒传奇巨星乔-迪马乔为主角。迪马乔有多传奇?这篇文章序跋就写得很清楚:
老人说道:“我希望能与迪马乔一同垂钓。”他接着说,“听闻迪马乔的父亲也曾是一名渔者。或许他昔日与我们境遇相似,生活困苦,因此我们或许能心有灵犀。”
这段文字摘自1951年海明威52岁在古巴创作的《老人与海》,正值迪马乔人生中最耀眼的时期。他的父亲确实是一位渔夫,而且据实,迪马乔家族或许从古至今一直从事着渔业。十年之后,海明威不幸因枪伤离世,又过了五年,特立斯以《英雄的沉默赛季》为题,为迪马乔的一生画上了句号。
与《一个美国篮球明星的故事》相异,在这篇正宗的“英雄特稿”里,英雄的赞誉踪影全无。当你翻阅特立斯的《英雄的沉默赛季》,满目皆是冷峻之色,而这冷峻之下,却蕴藏着无尽的同情。你所接触到的,是一个真实的人,而非神话中的英雄。
1957年,那位被誉为业界泰斗的比尔-海因茨,以50岁之龄,仅凭一篇特稿便获得了高达11500美元的稿酬。当他阅读了这位年轻人的作品后,不禁为之赞叹,其评价与《纽约时报》那位书评人如出一辙。他认为,特立斯的这篇稿子堪称佳作,其优点在于不仅向读者揭示了迪马乔的生平与生活,而且并未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他让读者与迪马乔相遇,然后自己去认知他。”
大卫-哈伯斯塔姆对该观点的推崇显而易见,他在编纂的《20世纪最佳美国体育写作》一书中,将首卷定名为“The Best of the Best”,其意不言而喻,即在20世纪杰出的体育写作中,再从中挑选出最为卓越的篇章。全书仅收录了4篇文章,特里斯的《英雄的沉默赛季》作为卷首之作,而沃尔夫的《最后的美国英雄》紧随其后——这里所说的沃尔夫并非《一个美国篮球明星的故事》的作者,而是被誉为“新新闻主义之父”的汤姆-沃尔夫。
至于哈伯斯塔姆这位人物,早在1963年,他就因对越战的报道而荣获了普利策奖的荣誉。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因对水门事件的卓越报道,被赞誉为“美国记者之父”。这位在政治和战争报道领域颇有建树的资深记者,身为一位经验丰富的老父亲,竟能编纂出一部关于体育写作的文集,并对其中内容有所评价,这本身就足以证明他在体育写作领域同样具有非凡的才华。他在1981年创作的《比赛间隙》一文,亦成为体育写作领域的经典之作,连美国当代著名的体育作家比尔-西蒙斯都曾不止一次地表示,《比赛间隙》对他的影响极为深远。
尽管美国拥有大量卓越的体育文学作品,然而实际上,最先引起中国读者关注的是《一个美国篮球明星的故事》。或许,这本书所采用的更贴近故事会的叙述手法,使得中国读者更容易接受。比如,这本书可能是首次将“有人能触及篮板边缘”这样的传说引入中国球迷视野的。或许关键因素依旧与环境相连,那时的中国读者对彼岸的职业体育了解不多,对于那个社会究竟是怎样的,也所知甚少。刚刚摆脱了非黑即白的观念束缚,对于一部强调价值观输出的美国作品,或许更能迎合中国读者尚未完全觉醒的思维方式。在那个时期,我们普遍倾向于依赖他人来揭示世界的真相,而不是通过自我探索去认识它。
《一个美国篮球明星的故事》一书虽评价平平,然而,三位译者吴月辉、瞿麟、朱世达的背景却颇为引人注目。自该书问世近40载,如今瞿麟在互联网上资料难觅,而吴月辉身为新华社资深编辑、全国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英语专家委员会委员,朱世达则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
吴月辉老师,作为全国翻译专业资格考试的命题专家之一,曾赴高校传授英汉互译的技巧,指出英译汉的难点在于对英文的准确理解,而汉译英的难点则在于如何恰当地用英文进行表达。吴老师指出,中英文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她特别强调,翻译的效果往往取决于细节的处理,“魔鬼藏于细节之中”(意指细节至关重要),精准的翻译工作需要深入挖掘词汇间的微妙区别,这便是所谓的“语言的微妙之处”。此外,吴老师还分享了一种“英译汉自检方法”,她建议:“若你发现所写的中文句子让人难以理解,那很可能说明你对原文的理解出现了偏差。”
在40年前,他翻译的那本名为《一个美国篮球明星的故事》的书中,曾提及霍金斯频繁运用自己的犹豫不决(实际上指的是move,即犹豫停顿步,具体可参考下图)来避开对手的追击。由此可见,吴老师似乎在那段时间还未创造出“英译汉自检法”。
当然,尽管书中存在一些与篮球专业术语相关的小错误,但整体阅读下来,这本小书的翻译非常流畅,读起来十分吸引人,依旧是一部翻译作品中的佳作。实际上,在1980年代的中国,翻译界还出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一些非翻译领域的人文学者也会参与到翻译计划的设立中,比如1980年负责策划《美学译文丛书》的美学专家李泽厚,在此之前他并未从事过正规的翻译工作。
在当时,寻觅一位精通体育的撰稿人负责翻译美国体育文章,这无疑是一种奢望。更不用说仅限于篮球这一细分领域,爱好者数量更是稀少。1979年,子弹队的随行人员也曾指出:“篮球在我国并非广受欢迎的运动。”
在这个子弹队访问我国的那个月,一位名叫程杭的年轻人诞生了。到了25年后的2004年,程杭从清华大学精密仪器专业毕业,随后在美国芝加哥建立了一个名为虎扑的篮球网络平台。该社区除了设有讨论区之外,其核心内容主要是由一群年轻人负责的外网篮球资讯翻译和新闻报道。这群人组成的团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翻译团”。十年之后,钟觉辰(网名三猎BERUS)将完成北师大文学院的本科学业。在步入研究生阶段的前夕,即2014年的夏日,他成功翻译了一部名为《The Book of》的著作。在此过程中,他将原本拟定的书名《篮史通贱》稍作修改,最终确定名为《篮史通鉴》,并正式出版发行。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篮史通鉴》的作者正是比尔-西蒙斯。
2020年夏日,距离华中科技大学光电专业本科毕业已有一年,程鹏(网名:朕铁打的江山啊,过往)在备战研究生入学考试之余,着手翻译了一部名为《The of The Game》的著作,即先前提及的《比赛间隙》。对于译稿何时能完工,以及能否顺利出版,程鹏并无确切预期,他坦言:“这仅仅是我出于个人兴趣而进行的翻译工作。”
自1979年至2020年,程杭至程鹏,诸多故事涌现,众多场景铺展,篮球从国与国交流的纽带,逐步转变为文化的象征,然而这一切巨变中,它不过是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在皮球经历的沧桑巨变之外,还有更难以捉摸的世界变迁,中美关系的跌宕起伏,篮球及其相关群体的命运亦随之起伏不定。
在过去的41年里,众多人士纷纷加入其中,有的乐在其中,有的则匆忙离场:我国转播商不再拖欠任何款项,2019年,腾讯与NBA签订的续约协议为期五年,总金额高达15亿美元;众多自媒体作者在网络上留下了自己的文字,短视频也成为了传播的新渠道。文字的魅力正逐渐减弱,新一代的读者很少再有耐心阅读一篇五千字的体育文章。在中国,严肃体育写作这一领域似乎从未真正崭露头角,其兴衰之快,宛如昙花一现。
那些岁月的见证者,郭永林未曾有机会踏入NBA的行列,甚至未曾涉足中国职业篮球的舞台;2009年8月,波林违背承诺,奇才队时隔30年重返中国,共同庆祝中美建交30周年纪念,然而他们未能与已故的挚友穆铁柱重逢,仅仅三个月后,老波林也离我们而去;2020年6月,昂塞尔德不幸离世……
在不久的将来,那些曾打破坚冰的回忆的持有者将相继离世,而他们所开拓的新世界,其继承者们正目睹着新的冰晶缓缓凝结,冰层逐渐加厚。在这冰层之上,有人心中黯淡,也有人欢歌笑语。

